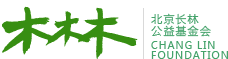联系我们
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
电话:(86)13810509559
邮箱:changlinjijin@163.com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北辰时代大厦1701室
徐门那些事
来源:未知作者:admin日期:2017/10/06浏览:
——记长林导师徐勇
文/秋晓
五月中旬,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敲开北京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办公室的门,他正和学生讨论第二天论文答辩的细节。
窗边的书桌上,放着厚厚一摞论文。随手翻开一篇硕士学位论文,写在最后“致谢”的文字颇动情:“师大最后的两年,能够踏入徐门是我天大的运气,也是我莫大的福气。徐老师广博深厚的学问底蕴,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,温和谦逊的处事风格,诲人不倦的教学风范,让我由衷地感受到‘导师’二字的分量。”
当了20多年老师,徐勇颇为在意学生的评价。他认为做老师最大的快乐和幸福,就是得到学生的认可和肯定。
徐门是徐勇学生的自封,其中有博士后、博士、硕士、本科生和访问学者。他们注册了QQ群——徐门群,发布相关消息、讨论问题之余,还会捣碎一些徐勇老师的轶事。他们以徐门弟子的身份自豪,最欢乐的事情就是一起去徐老师家聚会吃饭,天南地北的海聊。
2012年10月,徐门又增加了两名弟子,他们是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(以下简称长林)的两位荆门籍大学生——汪明和秦楚(均为化名)。在长林的一次导师见面会上,他们被分到徐勇的门下,他们说这全得益于长林的导师制。
导师制是长林的特色项目,即基金会在为荆门籍大学生提供经济帮助的同时,还为其配对导师陪伴成长,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。这项制度最早由徐勇提出,目前已有30多位导师,主要是荆门籍老乡,徐勇是其中一个。
2013年元旦前夕,汪明第一次参加徐门聚会。徐勇满屋的藏书给汪明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从客厅到书房,到卧室,再到阁楼的藏书室,每个房间中都堆着满满当当的书籍。书的类型非常丰富,有史书、有教育学的、有经济学的、有国际关系也有文学,整套房子就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。
聚会时,他们围坐在徐勇老师身边畅聊,聊书籍、聊历史、聊名人、聊时事、聊人生。谈话中,徐勇的一句话给汪明带来触动:“人是生活在不断行进的历史过程当中。”
他不禁回想起自己近期混乱的生活:每天只在宿舍里睡觉、看电影、玩游戏,已经很久没有拿起一本值得读的好书,在宁静的夜晚享受阅读的时光,“是该重拾以前的自己的时候了。”
自此,汪明跟其他徐门弟子一样,认为和自己的导师接触获益匪浅,“徐老师一些睿智、深刻的话,总能给我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和冲击。”
记者:北京长林公益基金的导师制是你最先提出来的,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?
徐勇: 一些荆门同乡最早提出成立基金会时,主要是想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荆门籍大学生,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资助。因为我在学校,和学生接触较多,对学生比较了解,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最需要的不是经济上的帮助,而是指导他们如何渡过大学四年。因为通过各种绿色助学通道,他们的经济问题已基本解决了,但怎样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,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人生,这些学生们则比较迷惘。再加上现在的各种诱惑多,对他们而言,精神上的引领比经济上的帮扶更重要,所以我提出要实行导师制,利用在京荆门籍人士的资源,给予来京的青年学子全方位的帮助。此外,我所在的北师大教育学部已经实行本科导师制,也给予了我直接的启示。
记者:这些想法,与你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?
徐老师: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我1979年到北师大历史系读书,那个时候只有16岁。虽说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学,但我能够离开农村已经很不错了,至于自己未来的路怎么走,自己想学什么,根本不知道。
记者:你参加高考比一般人早一些。
徐老师:是的,我上学比较早, 1977年恢复高考时,我还在上高一,学校觉得我成绩好,就让我去参加高考,为第二年正式参加高考积累点考试经验。1978年毕业的时候,虽然我考了京山县雁门口镇的文科第一名,但还是没考上大学,1979年才考上了。
记者:上大学后,当时是怎样的感觉呢?
徐勇:从小,学校哪个学生官最大,我就做那个,因为成绩非常,老师都非常关注我。来了北京,我就知道差距了。我们班的很多同学,都是往届积累下来的,年龄相差有10多岁,生活经历、背景差别特别大,同学中有的甚至是中学的校长,而我是一个来自偏僻农村的孩子。
身边没有任何熟悉的同学和亲人,年纪又小,思想还没有独立、成熟,所以时常觉得很迷茫,非常痛苦。
记者:上大学的时候,你有指导老师吗?
徐老师:学校没有指定,但老师资源的利用,完全在乎你自己。刚入学,我没有方向。我之所以选择学习历史文献学,是因为入校不久,恰逢学校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00周年,他研究的是历史文献学,很多老师都在讲他的学术,使得我对历史文献学产生了兴趣。不过,现在回首,我很高兴当初做了这样的选择,它对我现在的学术有很大影响。
选定方向后,我的心就特别专一,全心学习了文献学,把一些基本的书都读了,以至于两三年后,我能很骄傲地跟别人打赌:你只要说出任何一部古书的名字,我都知道它在目录学分类中属于哪一部哪一类?这个功夫很了不起,这样我找资料的时候会比别人快得多。
记者:在辅导学生过程中,你主要做什么事情?
徐老师:我把长林的学生,和学校分派我带的学生一体看待。但由于学生多,我基本处于被动的状态,即主要是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。学校分派的学生,指导学位论文是关键,长林学生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所以,如何带好长林学生,对于我来说,也是一个新的课题。我们很多长林导师,比如陈刚先生等人,对学生非常热心,而且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培养方法,值得我借鉴。
我对长林学生所做的,主要有两点:一是将他们纳入所谓的“徐门”,在聚会时一起参加,一些讲座也让他们前往。在这些活动中,和“徐门”的其他学生认识,这样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帮扶,有一个同门共同建立的成长环境。二是告诫他们,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宝贵的四年、是实现自我提升的最佳时机,在这四年里,要摒绝其他所好,专心致志地学习,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,开阔视野,优化素质,完善知识结构。与此同时,针对他们不同的专业,强调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,要把自己的专业放在整个人类知识的背景下来考虑,不要太狭隘,更不能作茧自缚。
记者:你闲的时候会干什么?
徐老师:不可能有那种情况。其实我现在最想没事做,好好地看闲书,以兴趣来决定看什么书。现在看书都是因为课题,都是实用性、功利性地看书,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。随心所欲地看一些书,这是最好的状态。我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,每天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拿一本书,随时随地的阅读成为了我的本能和习惯,我觉得把时间浪费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。
记者:到目前为止,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?
徐老师:你可能是指学术上的吧?这样两件事不知道是不是,算不算?在1992年9月,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登了一个招聘广告,向全世界招聘《中国文化通志》的作者。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讲师,试着投了一标,结果中了。记得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开笔仪式时,是李瑞环给我们发的聘书。后来,江泽民给这套书题词、作序,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十多个代表,其中我年龄最小。
还有一次,我要评职称,按照规定,每人至少要有一个科研课题。抱着广种薄收的心态,我同时申请了三个项目,一个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规划委员会的项目,一个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,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,最后这三个课题都被批准了。
文/秋晓
五月中旬,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敲开北京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办公室的门,他正和学生讨论第二天论文答辩的细节。
窗边的书桌上,放着厚厚一摞论文。随手翻开一篇硕士学位论文,写在最后“致谢”的文字颇动情:“师大最后的两年,能够踏入徐门是我天大的运气,也是我莫大的福气。徐老师广博深厚的学问底蕴,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,温和谦逊的处事风格,诲人不倦的教学风范,让我由衷地感受到‘导师’二字的分量。”
当了20多年老师,徐勇颇为在意学生的评价。他认为做老师最大的快乐和幸福,就是得到学生的认可和肯定。
徐门是徐勇学生的自封,其中有博士后、博士、硕士、本科生和访问学者。他们注册了QQ群——徐门群,发布相关消息、讨论问题之余,还会捣碎一些徐勇老师的轶事。他们以徐门弟子的身份自豪,最欢乐的事情就是一起去徐老师家聚会吃饭,天南地北的海聊。
2012年10月,徐门又增加了两名弟子,他们是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(以下简称长林)的两位荆门籍大学生——汪明和秦楚(均为化名)。在长林的一次导师见面会上,他们被分到徐勇的门下,他们说这全得益于长林的导师制。
导师制是长林的特色项目,即基金会在为荆门籍大学生提供经济帮助的同时,还为其配对导师陪伴成长,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。这项制度最早由徐勇提出,目前已有30多位导师,主要是荆门籍老乡,徐勇是其中一个。
2013年元旦前夕,汪明第一次参加徐门聚会。徐勇满屋的藏书给汪明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从客厅到书房,到卧室,再到阁楼的藏书室,每个房间中都堆着满满当当的书籍。书的类型非常丰富,有史书、有教育学的、有经济学的、有国际关系也有文学,整套房子就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。
聚会时,他们围坐在徐勇老师身边畅聊,聊书籍、聊历史、聊名人、聊时事、聊人生。谈话中,徐勇的一句话给汪明带来触动:“人是生活在不断行进的历史过程当中。”
他不禁回想起自己近期混乱的生活:每天只在宿舍里睡觉、看电影、玩游戏,已经很久没有拿起一本值得读的好书,在宁静的夜晚享受阅读的时光,“是该重拾以前的自己的时候了。”
自此,汪明跟其他徐门弟子一样,认为和自己的导师接触获益匪浅,“徐老师一些睿智、深刻的话,总能给我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和冲击。”
记者:北京长林公益基金的导师制是你最先提出来的,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?
徐勇: 一些荆门同乡最早提出成立基金会时,主要是想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荆门籍大学生,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资助。因为我在学校,和学生接触较多,对学生比较了解,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最需要的不是经济上的帮助,而是指导他们如何渡过大学四年。因为通过各种绿色助学通道,他们的经济问题已基本解决了,但怎样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,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人生,这些学生们则比较迷惘。再加上现在的各种诱惑多,对他们而言,精神上的引领比经济上的帮扶更重要,所以我提出要实行导师制,利用在京荆门籍人士的资源,给予来京的青年学子全方位的帮助。此外,我所在的北师大教育学部已经实行本科导师制,也给予了我直接的启示。
记者:这些想法,与你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?
徐老师: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我1979年到北师大历史系读书,那个时候只有16岁。虽说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学,但我能够离开农村已经很不错了,至于自己未来的路怎么走,自己想学什么,根本不知道。
记者:你参加高考比一般人早一些。
徐老师:是的,我上学比较早, 1977年恢复高考时,我还在上高一,学校觉得我成绩好,就让我去参加高考,为第二年正式参加高考积累点考试经验。1978年毕业的时候,虽然我考了京山县雁门口镇的文科第一名,但还是没考上大学,1979年才考上了。
记者:上大学后,当时是怎样的感觉呢?
徐勇:从小,学校哪个学生官最大,我就做那个,因为成绩非常,老师都非常关注我。来了北京,我就知道差距了。我们班的很多同学,都是往届积累下来的,年龄相差有10多岁,生活经历、背景差别特别大,同学中有的甚至是中学的校长,而我是一个来自偏僻农村的孩子。
身边没有任何熟悉的同学和亲人,年纪又小,思想还没有独立、成熟,所以时常觉得很迷茫,非常痛苦。
记者:上大学的时候,你有指导老师吗?
徐老师:学校没有指定,但老师资源的利用,完全在乎你自己。刚入学,我没有方向。我之所以选择学习历史文献学,是因为入校不久,恰逢学校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00周年,他研究的是历史文献学,很多老师都在讲他的学术,使得我对历史文献学产生了兴趣。不过,现在回首,我很高兴当初做了这样的选择,它对我现在的学术有很大影响。
选定方向后,我的心就特别专一,全心学习了文献学,把一些基本的书都读了,以至于两三年后,我能很骄傲地跟别人打赌:你只要说出任何一部古书的名字,我都知道它在目录学分类中属于哪一部哪一类?这个功夫很了不起,这样我找资料的时候会比别人快得多。
记者:在辅导学生过程中,你主要做什么事情?
徐老师:我把长林的学生,和学校分派我带的学生一体看待。但由于学生多,我基本处于被动的状态,即主要是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。学校分派的学生,指导学位论文是关键,长林学生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所以,如何带好长林学生,对于我来说,也是一个新的课题。我们很多长林导师,比如陈刚先生等人,对学生非常热心,而且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培养方法,值得我借鉴。
我对长林学生所做的,主要有两点:一是将他们纳入所谓的“徐门”,在聚会时一起参加,一些讲座也让他们前往。在这些活动中,和“徐门”的其他学生认识,这样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帮扶,有一个同门共同建立的成长环境。二是告诫他们,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宝贵的四年、是实现自我提升的最佳时机,在这四年里,要摒绝其他所好,专心致志地学习,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,开阔视野,优化素质,完善知识结构。与此同时,针对他们不同的专业,强调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,要把自己的专业放在整个人类知识的背景下来考虑,不要太狭隘,更不能作茧自缚。
记者:你闲的时候会干什么?
徐老师:不可能有那种情况。其实我现在最想没事做,好好地看闲书,以兴趣来决定看什么书。现在看书都是因为课题,都是实用性、功利性地看书,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。随心所欲地看一些书,这是最好的状态。我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,每天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拿一本书,随时随地的阅读成为了我的本能和习惯,我觉得把时间浪费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。
记者:到目前为止,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?
徐老师:你可能是指学术上的吧?这样两件事不知道是不是,算不算?在1992年9月,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登了一个招聘广告,向全世界招聘《中国文化通志》的作者。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讲师,试着投了一标,结果中了。记得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开笔仪式时,是李瑞环给我们发的聘书。后来,江泽民给这套书题词、作序,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十多个代表,其中我年龄最小。
还有一次,我要评职称,按照规定,每人至少要有一个科研课题。抱着广种薄收的心态,我同时申请了三个项目,一个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规划委员会的项目,一个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,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,最后这三个课题都被批准了。
相关文章
- 2022/08/30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十周年庆典活动圆满
- 2021/09/28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2021年励志奖学金评审
- 2021/07/13庆祝建党一百周年——北京长林公益基金
- 2021/07/13北京长林公益基金会祝各位爱心人士端午
- 2021/07/13世界读书日,一起来阅读吧!